音樂的磁吸
(1932-1949)
●漢文老師的大家庭
我的父親是村裡著名的漢文老師,他出生時,臺灣還是清朝的領土。父親小時候唸私塾,四書五經都讀過,浸淫在漢文化裡長大,一心想要考秀才。1894年甲午戰爭後,一切起了變化。1895年,中日簽訂馬關條約,臺灣被割讓給日本,在殖民統治下,大環境改變了,對我們家影響很大。
家裡原本開有酒廠,賣酒跟酒糟,那時生意做很大,也有賣到福州去,哥哥還被派去福州管分公司。日本人統治時,將酒改成專賣,酒廠無法繼續經營;我小時候喜歡在大酒缸裡玩,長大後,才知道家中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大酒缸。酒廠收起來,固然影響家中生計,但還可以靠收佃農租金維持生計。我記得小時候家裡附近有土城庄的「組合」,這是個像現在農會的組織,「組合」裡有碾米設備,稻穀經過碾米機碾成白米後,從機器尾端小孔送出來,在白米出口處有一個活動孔蓋,開開闔闔的,看起來很好玩,我覺得很好奇,就用手把孔蓋壓住,讓稻米出不來,於是整臺機器就停掉了,碾米的阿伯看到,追著我邊跑邊罵。現在想起來,我小時候真的很調皮。
對父親而言,日本人來,更痛心的事情是科舉制度被廢除,考秀才的願望落空,終生遺憾。也因為這些原因,父親很恨日本人,也始終認同漢文化,絲毫不受外在大環境影響。甚至在戰爭時期, 物資缺乏的年代,臺灣人如果改日本姓,可以有特別配給,對於人口眾多的家庭,引誘力不可謂不大,但是父親從不考慮改姓。他的堅守漢文化,更可以由他熱中於教授漢文一事看到。
日本人來了後,沒有了教漢文的私塾,不過,還是有許多人想學漢文。父親教漢文不以營利為目的,只要有心學,他一概傾囊相授,學費完全不是問題。他的漢文學生遍及各種年齡層, 也有日本人,甚至還有日本警察,他們會腰間配著刀來上課。我們家那時可以說是土城地區的漢文中心,鄉里都非常尊敬父親, 稱他「查某仙」,這個稱呼是有來頭的。
據兄長陳述,父親是早產兒,小時候體弱多病,當時的迷信是取一個不雅的叫名,會幫助小孩健健康康地成長,於是就叫他「查某囡仔」,果然父親健康地長大了。成年後,大家仍習慣叫他「廖查某」,後面加個「仙」,是老師的尊稱。漢文學堂的興盛,也讓我們家人來人往,非常熱鬧。
學生們來上課時,會帶來各式各樣的束脩,聊表心意,就像古時的傳統一般。在物資缺乏的年代裡,學生們的束脩還是很重要,例如有些學生會帶自己家中養的雞來,直到今天,我都還記得雞腿的可口美味。
父親以閩南語教漢文,帶大家唸三字經、千字文、論語等等漢學經典。他不僅教他人,也要求子女學漢文。父親教子女的方式,匠心獨具。他為我們每個孩子各準備一本專屬教本,由三字經開始教,之後是千字文,每天教完一句,就畫上紅圈記號。每個人的學習情形不同,書本上的註記也會有所不同,所以每個人都要有一本自己的教本。我從小就很會背誦,學東西很快,所以很得父親歡心。
每每父親晚上有空時,會帶著我一同走路去土城,大約要走個廿多分鐘。一路上,父親會要求我將最近幾天教的書背給他聽,如果背得好,到了土城街上,就有好吃的東西獎賞。在父親的教導、要求和鼓勵下,我用閩南語背了許多古文。除了背古文外,父親還教我們用毛筆寫書法。後來上日本國校時,學校也有教毛筆寫字,但是,日本老師教的拿法跟拿鉛筆一樣,讓我很不習慣。或許是物資缺乏吧,在家裡,是用報紙摺出格子練習寫書法。
雖然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不長,但是感謝他的教導,讓我在那個時代,還可以在充滿漢文化的環境長大。不僅如此,那時沒有人會想到,這些漢文對我日後的升學,竟有很大的幫助。
父親留給我的回憶,除了漢文外,還有音樂。父親有位朋友阿壽叔,在「臺北放送局」工作。這個單位由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於1930年成立,位於新公園,即是今日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所在。「臺北放送局」的主要目的在於政令宣導,但是,對年幼的我來說,它讓我聽到許多歌曲,可說是我音樂啟蒙的開始。阿壽叔來家裡做客的時候,都會教我唱日語歌,唱個一兩遍,我就學會了。今天回想起來,他可算是第一位讓我展現音樂才能的長輩。或許也是這樣,我至今都還記得阿壽叔,他當年教我的歌,我也還記得: 阿壽叔教我唱的是《旭日東升》。
不僅如此,我自己聽收音機廣播時,也學會唱些曲子,有一首是《海之歌》。這些曲子,黃靖雅寫碩士論文時,還真的找到了曲譜,不過歌名有些出入,前者是《愛國行進曲》,後者是《海行かば》。
為什麼有這些差別,我不知道,或是後來出版歌曲集時,曲名改了。今天回頭想來,這些歌曲不外乎是日本軍歌及愛國歌曲,歌詞裡反映了濃濃的日本帝國主義思想,只是我那時候年紀小,好聽的是旋律,自己能很快學會、記住,至今都還能流利地唱出,是人生的一件得意事,至於歌詞在說什麼,當時就未在意,今天更記不得,也更無所謂了。
除了廣播外,電影音樂提供了另一個聽歌的來源。2011年下半年,我看到電視報導李香蘭的電影《莎韻之鐘》,聽到主題曲的旋律,驀地想起,幾十年前,我曾經與哥哥在臺北延平北路的第一劇場看過這部電影。當年,哥哥廖年豐偶而會帶我去臺北看電影,他騎腳踏車,我坐在前面橫桿上,坐上半個小時,到達臺北時雙腳又麻又疼,但是能看電影,就很開心了。
就算沒能跟去看電影,哥哥姐姐們看完電影留下來的「本事」(Program),我會小心收藏起來,不是因為上面的劇情說明,而是因為上面有電影配樂的簡譜。我還記得,曾經在日本電影裡,看到過指揮帶領小樂團演出的畫面,只是我家全無音樂背景,那時候看到,並沒什麼太多感覺。
雖然父母早逝,但是我有很多兄姐,而且因為我是么子,兄姐都很疼愛我,他們很早就代替了父母的地位,一路照顧我成長。
多元的音樂工作嚐試
(1952-1983)
●與省交結緣(1955-1973)
由於拉小提琴,我經常去中華路新麗聲樂器行買絃、松香等器材,認識了樂器行的老闆楊朝開。楊朝開任職於省交,他打大鼓, 也拉大提琴,卻沒有正式學過大提琴。他知道我拉小提琴,在空小教書,勸我轉到樂團工作,輕鬆很多。對我來說,是否輕鬆並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可以整天拉琴,這是當時我的最愛。1955年,有一天,我依楊朝開建議,帶著小提琴,到省交應試。當時的團長是王錫奇,考試時,他問我的師承,聽到是戴粹倫,就說不必考了,直接入團。我很開心地辭掉空小教職,加入省交,一待就是十八年。
省交那時的全名為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,是臺灣的第一個交響樂團,今天名為「國立臺灣交響樂團」,簡稱「國臺交」; 我還是習慣稱它「省交」。樂團成立的背景與多次改名的過程, 都和臺灣政治環境的變化有直接的關係。
1945年十二月一日,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軍簡二階少將參議蔡繼琨籌組成立了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」,並任首任團長。蔡繼琨家族世代居於臺灣鹿港,祖先曾為同治年間進士。甲午戰爭後,臺灣被割讓給日本,蔡家舉家遷居泉州,卻世代不忘要回臺灣。蔡繼琨於廈門集美師範學校畢業後,至日本東京帝國高等音樂學校留學,並曾以《潯江漁火》作品獲得日本國際作曲家協會交響曲比賽大獎,很有音樂才華。陳儀任福建省長期間,蔡繼琨為其主持藝文工作。抗戰勝利後,蔡繼琨隨陳儀來臺,擔任臺灣省受降典禮委員。因著職務之便,大力成立交響樂團,並恢復舉辦臺灣省美展,對於甫光復的臺灣藝文環境的建立,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1949年,蔡繼琨奉派赴菲律賓任大使館參贊,自此甚少回台。1983年,蔡繼琨回泉州定居,並任福建音樂學院院長;2004年三月於當地過世。簡言之,陳儀當年負責接收臺灣以及之後的統治事宜,固有多方不適任和錯誤的政策,但藝文界不能不感謝他信任蔡繼琨,才能奠下臺灣藝文發展的基礎。
臺灣甫光復之時,百廢待舉,樂團絕不是首要之務。感謝蔡繼琨的魄力之舉,光復後不久,樂團就成立了,團員亦授予軍階。不久之後,1946年(民國三十五年)三月,全國裁軍會議決定裁撤,有心人士努力下,將樂團改隸於行政長官公署,亦隨之改名。1947年(民國三十六年)二二八事件後,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,樂團再度改名,於1948年(民國三十七年)元月改名為臺灣省立交響樂團。
同年年底,省府參議會提議撤除交響樂團,幾經交涉,將樂團管樂隊改列省府軍樂隊,管絃樂隊改隸臺灣省建設協會。蔡繼琨調任菲律賓後,軍樂隊長王錫奇接下團長,再經多方努力後,1951年(民國四十年),樂團終於又隸屬於省政府教育廳,更名為「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」,直到我進樂團時,還是這個名字。
進省交後,由老團員那裡聽到很多故事,印證了省交成立的特殊背景。有人曾經告訴我,當年日本人被遣返時,有些團員就拿著蓋有行政長官公署交響樂團印章的紙,貼在空屋門口,佔為己有, 成為自己的住家。
也正因為倉卒成軍,團員素質不齊,管樂的來源有軍樂與「西索米」(就是送葬管樂團之俗稱)樂隊手,絃樂則極端缺乏,要不就是管樂手臨時去學絃樂,要不就得對外招考,才會有楊朝開告訴我的事。我進樂團時,是全團最年輕的團員,被分在第一小提琴聲部。樂團首席是臺南人黃景鐘,跟一位由日本回來的老師蔡誠絃學,也是科班出身。黃景鐘經驗豐富,我坐在他後面, 學到很多,很有收穫。
那時的省交位於西本願寺,俗稱「大廟」,亦即是今日的西門町、中華路底。我還記得,第一天的排練曲目是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,由王錫奇擔任指揮。對當時的樂團而言,算是很難的曲目。也是因為這首「貝七」,我不久後離開省交好一陣子。
到省交工作後,才瞭解楊朝開說的「輕鬆」是什麼。樂團倉促成立,團員水準良莠不齊,上班時衣衫不整,穿著短褲、背心就來的人比比皆是;也有人有著當時俗稱「國恥」動不動就吐痰的習慣。排練中間休息半個小時的時間,不少團員蹲在地上抽菸、吐痰、聊天,不然就是標會、收錢。團練或音樂會時,演出的音樂慘不忍聽。省交剛開始經常演奏史特勞斯的圓舞曲,還都是簡易版。
諸此種種,都和我對樂團的期待相距甚遠。進省交一年多後,有次練貝七,貝七前面的主題是六八拍,樂團卻總是演奏成附點四分音符加八分音符,聽起來很不舒服。我知道這樣下去,樂團程度不可能好,上班很痛苦,乾脆就不去了。大約四個月後,省交當時的演奏部主任陳暾初帶她女兒去市立女中(現在的東門國小)比賽,我也帶學生去比賽,兩人在那裡相遇。陳暾初知道,我因為樂團程度太差,很不滿意,才離開樂團,他告訴我,第二年三月左右,美國國務院會派一個指揮來,希望我再回團裡。我聽了他的話回省交,樂團竟將離開四個月的薪水都算給我,好像我沒有離開過,讓我很驚訝,也有些不好意思。
第二年,1958年五月,果然指揮約翰笙(Thor Johnson)來了, 剛好也指揮貝七,終於把節奏一一調整好了,樂團水準提升很多。約翰笙來省交指揮後,認為王錫奇帶團不行。
當時的教育廳長為劉真,他曾經做過八年師大校長,在聽了建議後,邀請師大音樂系系主任戴粹倫來兼省交團長。那個時代,一個人兼好幾樣專職是常事。
不僅如此,劉真還立刻撥了一百萬經費給省交,五十萬買樂器,五十萬在師大運動場邊蓋一個練習廳,就是音樂系第二代系館。1959年,戴粹倫任團長後,逐步整頓省交,最早的團員依制度慢慢地淘汰。當時樂團的帳很亂,戴粹倫不放心,要我任出納,老師開口,我雖沒經驗,卻也不敢說不,只能努力做,這可算是我第一個行政經驗。1969年,我開始兼任演奏部主任,參與更多樂團行政工作。
約翰笙在的時候,省交就已在國際學舍開音樂會了。戴粹倫接團長後,和國際學舍簽合約,讓樂團能有定期演出的場地。大約每六到八星期,省交就在臺北有一次大規模音樂會。那時候沒有什麼音樂活動,省交每次演出都可說是樂壇盛事,引人注目, 我的管絃樂作品《中國組曲》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被演出的。
省交慢慢交出像樣的成績單後,戴粹倫著手逐步擴展樂團的活動面向。1965年開始辦暑期音樂研習會,招收年輕學生,並在研習會結束時,舉行成果發表會,甚受讚賞。1965年11月,戴粹倫正式將這些學生們組成「省交響樂團附屬小弦樂團」,並於1966年二月廿六日於臺北國際學舍舉行成立後首次音樂會。1972 年底,因省交南遷臺中及戴粹倫辭去團長兼指揮之務,小絃樂團隨之宣告解散。無論是暑期音樂研習會,還是小絃樂團,戴老師都要我參與工作,讓我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,終身受用。尤其是我自己在1968年創辦了「世紀」,一切由零開始,若無省交的經驗,一定是焦頭爛額,樂團亦不可能順利地成長。
省交搬到臺中後不久,我也離開省交,走向另一條音樂路。雖然離開了,對這個樂團總是有著特別的感情,畢竟它在我的音樂人生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。它不僅提供我拉小提琴謀生的可能,更讓我認識樂團內內外外的點點滴滴,也讓我開始思考其他的音樂前途。在臺灣精省的過程中,省交再次經歷了一段困難的時期,有需要我幫忙時,我總是盡己所能,義不容辭,披掛上陣,希望能略盡棉薄之力。省交六十年團慶時,邀請我寫些話, 也讓我覺得很榮幸。
多年下來,團裡人事早已全非,年輕的一代無論在音樂知識或技能上,都比我們這一代好很多,希望這臺灣第一個公設樂團,能在他們的努力下,長長久久,愈來愈好,對臺灣的音樂環境有更多貢獻。
精益求精:出國進修
(1976/77, 1990/91)
●前進維也納(1976-1977)
1973年,我離開了省交。在省交時,我心裡就很明白,自己的音樂程度並不夠好,要帶好樂團是很勉強的。但是,我並不知道該怎麼做比較正確。辭去省交的工作時,我最想立刻做的事,是去維也納,這個號稱「音樂之都」的地方。不過,那時我已41歲,而維也納的學校不收年齡超過25歲的學生。而且離開省交,沒有專職,也就沒有固定收入。那時我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,總得考慮家庭的問題。
好在盧寧一直很支持我在音樂路的任何決定,只要能夠出國進修,她總是全力支持。我們商量好,我出國時,她暫時負責照顧家庭,並繼續隨蕭滋教授學習鋼琴,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。至於出國的經費,很幸運地,兄姐將祖產賣掉,每人都分到一筆錢。對我來說,真是及時雨,感謝老天!
除了家庭和經濟財源的考量之外,那時候還有另一個困難,要出國必須經過層層管制。雖然每個人都可以申請護照,但是必須要有理由,這個理由要經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,才能真正地申請護照。在取得護照後,才能申請要前往國家的簽證。所以從打算出國到真正能出國,究竟需要多少時間,很難控制。不像現在,辦護照、簽證都很快,有效時間還很長,許多國家連簽證都不必先辦,要出國,買張機票就出發了。正因為這一層層的困難要克服,雖然計劃去維也納,卻不是一時半時可以做到的。於是我在教學生、帶樂團之餘,同時開始規劃,要如何一步步地達成目標。
1972年,我開始在中國文化學院(今天的中國文化大學)兼任,教小提琴。在那裡,我認識了柯尼希(Wolfram König),他已在文化教了很多年小提琴,也算是當時的名師。我不是很清楚柯尼希是怎麼來臺灣的,我還記得,他太太拉中提琴。我曾邀請柯尼希與世紀合作,演出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,他相當滿意。柯尼希後來要回德國,他讓陳必昭(陳必先的妹妹)轉來跟我上課。
柯尼希建議我,要趕快去維也納,跟隨維也納音樂院最好的指揮教授斯瓦若夫斯基(Hans Swarowsky, 1899-1975)學。可惜的是,在我終於可以去維也納的時候,斯瓦若夫斯基過世了。我到維也納,就只能跟隨他的學生奧斯特萊赫(Karl Österreicher, 1923-1995)。後來很多年輕一輩的臺灣學生,也都跟過奧斯特萊赫學習指揮。
既然目標是跟斯瓦若夫斯基學, 就得進維也納音樂院(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in Wien)。由於已經超齡,我根本不可能以學生的身份進去。這時,在臺灣的音樂關係發揮了功效。蕭滋老師以前的鋼琴學生張瑟瑟那時已經在維也納,她在臺灣時,因為蕭滋老師要求要演奏室內樂,我們曾經合作演出室內樂音樂會。張瑟瑟提供訊息,願意在維也納幫我辦理旁聽學生證,整個出國手續有了曙光,踏出第一步。我至今都很感謝她當年的幫忙。
於是我開始申請護照。當年申請出國的理由不是留學,而是出國考察。那時我是亞洲作曲家聯盟(簡稱「曲盟」)的理事,由曲盟出公文推薦我去奧地利考察,用這個理由向主管機關教育部申請,獲得核准後,順利取得護照。到了維也納之後,再請張瑟瑟幫忙,介紹指導教授奧斯特萊赫,由他出面辦理旁聽生證。
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奔波,1976年九月,我終於如願到了維也納,成為維也納音樂院的旁聽生。旁聽生一樣要繳保險費,沒學分也沒學位,什麼證書、證明都沒有。對我來說,這些都不重要,我的目的是要真材實質地學,學我還不知道的東西,補強過往的不足。
為了準備到當地上課,我在臺灣就開始學德文。那時候要找到人學德文,也不是件容易的事,我是跟一個叫白衛理的瑞士記者學,他可以說一口流利的中文。好在有這麼點基礎,到維也納後,在學校課堂上講德文,在奧斯特萊赫家上個別課時,則是講英文。有著當年跟蕭滋老師上課的經驗,我一點都不怕語言不夠好,至少溝通、瞭解老師教的東西,是沒有問題的。
白天在學校,老師用德文上課,我不是完全聽得懂,於是請老師在他家裡用英文一對一上課,有時候一星期會上兩次。
由於只計劃去維也納一年,一定要全力認真學,所以,時間和精力都擺在看譜和練習上。明知道有很多好聽的音樂會,只能挑很重要的場次聽,不敢每場都去。我以前的學生陳泰成那時也在維也納,他對我說:「廖老師,你不能整天待在家裡,會生病的。」於是他硬逼我搭他的車,開到維也納森林去散步,結果,車開到那裡,他去散步,我留在車上看譜。我這麼拚,是有原因的,因為每個星期要去老師那裡上課,課前一定要將譜看熟才行,否則上課學不到什麼。畢竟自己已不年輕,出國進修,是知所不足,當然要用功才行。
嚴格來說,我開始學指揮,是到維也納之後才真正開始。當年跟蕭滋老師上課時,和聲學、作曲、指揮都在學,指揮當然不可能學得很紮實。好不容易來到維也納,當然要從基礎開始,紮實地學。我們一班有十七個人,其中有很多已經有指揮經驗。奧斯特萊赫很嚴格,無論是否有指揮經驗,一律由基本姿勢和動作開始要求。
我們練習的第一首作品是莫札特小夜曲,一開始,大家都覺得很簡單,奧斯特萊赫經驗老到,他告訴我們,不要小看這首曲子,要從簡單開始,才能打好基礎。慢慢地,我瞭解到,蕭滋老師教我的東西,其實是已經有基礎以後的教法,基礎不足,只能「知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」。奧斯特萊赫傳承自斯瓦若夫斯基,後者見長的小節句分析,只有他的嫡系學生才學得到。跟著奧斯特萊赫上課,當然也會學到這種分析方法,我發現指揮只要把小節句背熟了,就不會出錯。斯瓦若夫斯基系統的指揮,舉手投足、音樂詮釋,一看就知道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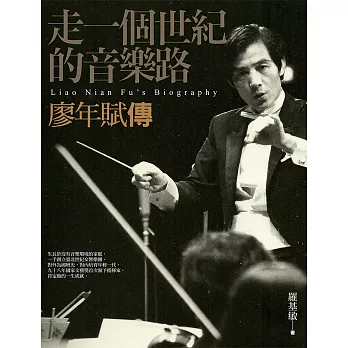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