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世界的盡頭,我們學跳舞
Her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Learn to Dance
- 作者: 羅伊德.瓊斯
- 原文作者:Lloyd Jones
- 譯者:陳錦慧
- 出版社:聯合文學
〈第1章〉
有位拄著銀柄手杖的老人家,連續十一年帶鮮花去給露易絲上墳。他每星期六都會出現,提著塑膠桶、刷子、清潔劑和一把帆布折疊椅。他出現的時候總是打扮得體,黑色休閒外套、白色長褲,外套釦眼上的鮮紅花朵跟一頭白髮形成強烈對比。
過世前那一年,他習慣帶十歲小孫女造訪恰卡里達墓園。他坐在露易絲的墳墓旁、用軟呢帽搧涼時,小孫女就提著塑膠桶,跟其他前來追悼亡者的人一起在水龍頭前排隊。
保羅.施密特自己有車,可是,在這趟特殊旅程中,他喜歡搭公車。司機會扶他下車。在舞池裡時,他的腳步從來不曾如此遲疑、如此猶豫。他總會聽見一聲叮嚀:「先生,小心車子。」他會不以為然地咕噥一聲,然後舉步橫越川流不息的馬路,朝狄亞茲上校大道的鮮花攤走去。
以一個生命核心裡隱藏了重大欺瞞的人而言,施密特在許多生活小細節上展現忠誠度,並以此自豪。比如說那個特定的公車司機,以及那個他買藍色鳶尾花的巴拉圭籍鮮花攤小販。
某個星期六,另一個鮮花攤陳列的花束吸引他的目光,是黃花毛茛和金雀花,喚醒一段陳年回憶。當時公車還在行駛,他費力地從座位上站起來,踉踉蹌蹌地越過鄰座女士的膝蓋。公車猛地顛了一下,他急忙用雙手抓住擺盪不迭的吊環,手杖嗒啦啦地掉落走道,他卻毫不在意。事後,公車司機說他看見施密特彎低身子、隔著公車後車窗凝望那束盛開的金雀花漸漸遠逝的影像,一手按住某個婦人默默承受的肩膀、穩住腳步。
到了下一站(他平時不是在那裡下車),施密特跌跌撞撞走下公車。司機從後面追上來,把手杖遞還給他。老人瞥了手杖一眼,沒道謝就收下。司機笑了笑。他們彼此心領神會,或者說,他們生命中特定的兩段時刻已經成了他們友誼的基礎。其一是老先生上車下車的時點;另一個重要時刻落在聖誕節前一星期,那時老先生會給司機一盒高檔雪茄。雪茄總是最後一刻才出現,等公車減速,緩緩駛進老先生的站牌,老先生才匆匆遞出,動作爽快直接,彷彿遞出不需要的物品似的。司機收下雪茄時則是連聲道謝、過度謙遜。
- 此時,司機從公車車窗裡看著老人穿越繁忙的車道。他看見老人用手杖指著朝他接近的車輛。事後,那個賣花小販會說,老先生的「眼睛、臉孔和記憶緊緊鎖定我的花束。」(注意,不單單圍繞著盛開的嫩黃金雀花,而是他親手搭配的花束。)「沒有看見從另一個方向駛來玻璃瓶運輸車。」同一時間,在公車車窗裡的司機從喉嚨發出空洞的警告聲,然後閉上雙眼,不忍目睹最後那一刻的衝擊。這段過程司機會再三重述:首先,老先生閃神了;緊接著,血液一股腦地湧向老先生頭部;最後,是老先生的任性而為。常規打破了,聖誕節不再有雪茄。這段故事頗有警世意味。
〈第2章〉
死亡裡沒有祕密。在恰卡里達墓園,富人們安葬在法老等級的巨大陵墓裡,那些陵墓仿效知名禮拜堂的風格打造而成,水泥和石膏雕塑的天使與魯特琴演奏者踮著腳尖旋轉,聖經故事場景大手筆地雕刻在石材上。若說富人死後仍得繼續享受奢華,那麼窮人也同理可證,他們一個接一個、這個疊那個,像三明治般擠進壯觀的墓穴牆裡,這些年代較為久遠的墓穴形成了墓園內牆。新一批墓穴是某個購物中心開發商建造的,遺體堆疊在一個接一個的墓室裡,階梯深入地下二到三層樓,底下有工作枱,也有身穿藍色工作服、肩扛掃把的墓園工人。窒悶的空氣裡彌漫著塞在棺木把手上凋零花朵那令人作嘔的氣味。
施密特什麼都買得起,他的遺孀原本有意選購一座小型家族墓穴,或許以管弦樂器為主題,彰顯家族事業。
沒想到,施密特留下遺言,要長眠在他那位忠心耿耿的助理身旁,而且喪禮從簡,讓他太太無比震驚。助理就是那個「說英語的女人」,生前樸素沉默,施密特太太只知她名叫露易絲。
她們倒是交換過幾句客套話。合宜的對談往往格外耗費心思,何況那女人的西班牙語充其量只有幼兒程度。上街採買的時候,她直接指著她要的東西,讓話語從手指末端延伸而去。如今施密特太太努力回想她們每次碰面的情景,發現過程都很短暫,沒有留下任何特別顯著或具啟發性的印象。
有一回碰上夏季暴風,搭計程車時她堅持要施密特順道送「助理」回家,她記得當時抬頭望見一棟灰色建築,上面有粉紅色與藍色的石膏浮雕(她依稀記得是玫瑰形花飾)。助理的臉蛋突然伸進車窗來,感謝她好心送她回家。助理的頭髮又濕又亂,臉上的妝容被雨水沖落,一道暗色眼線殘漬從一邊眼角流淌而下。實在算不上什麼美人胚子。
- 露易絲過世十一年了,不過,有個老婦人──她生前的鄰居──仍然記得那個「說英語的女人」,也記得那女人獨來獨往。老婦人大聲說道:「她不會說話。」不,她也不交朋友。「那麼訪客呢?她訪客多嗎?」老婦人陷入沉思。施密特的遺孀一度考慮塞錢給對方,可老婦人又說話了。「不多,沒有很多。不過有一個……」她開始描述施密特太太剛過世的丈夫:滿頭白髮、光滑的臉龐、栗色眼珠、拄著手杖,衣著考究。「太太,妳也知道的,有些人走到生命盡頭時已經征服了歲月,其他人離開人世時卻還在跟時間賽跑。那位先生屬於前一種類型。」這段對話的地點在樓梯口,走道另一端傳來水龍頭滴水的聲音。整棟建築破敗不堪,她丈夫向來講究,她無法想像他會出現在這裡,在這個樓梯間。她沿著走道往前走,然後停下來,回頭確認。「是最裡面那間嗎?」老婦人點點頭。「是的,太太,就是那間。」她心想,丈夫一定也看見過眼前的景象,看見過盡頭那扇窗外面那抹清冷斜光、同樣的木地板在他腳底下嘎吱嘎吱響。可是他心裡有什麼感覺呢?興奮嗎?心花怒放?老婦人趕了上來。「太太,妳願意的話,我可以帶妳看看院子。那位先生和那個外國女人偶爾會坐在花園那棵酸橙樹下。很可惜,樹已經沒了……」
施密特的遺孀搖搖頭。她看得、聽得都夠多了,想要離開了。「還有一件事。」老婦人說起房東派人運走那女人遺物時的情景,突然露出淘氣神色,把臉靠過來低聲招認,「我也很好奇,所以探頭進去偷瞄一眼。」裡面沒什麼東西,一台唱機,一疊唱片,一些衣服,一雙黑色細跟高跟鞋。「就是那種在愛迪歐舞廳跳舞的人會穿的鞋。」施密特太太也有朋友在愛迪歐跳舞,她不免尋思,她的朋友們是不是見過她先生和那個助理,只是選擇三緘其口。老婦人又說話了:她自己房間總是亂糟糟的,可一走進那個女人的房間,你會注意到她的地板,很顯眼。你會看見那長長的木板,還有客廳正中央那些「刮痕」。施密特太太提出下一個問題時,只覺雙眼一陣酸楚,但她不能不問。「妳是想告訴我,她跟那位先生喜歡跳舞?」老婦人大幅度擺動雙手。「跳舞?他們一直跳,一直跳。喔,他們跳個不停。跳完就坐在花園裡休息,接著又多跳一會兒。那個女人不說話,她只跳舞。」
……
- 〈第6章〉(選摘)
開始時果然免不了幾句責難。羅莎說我沒有在舞步裡注入任何東西,沒有情感,也沒有說服力,說我根本就像把牛奶瓶拿到屋外。不對,牛奶瓶這個比喻不好。她說,「你就像在水底游泳,每隔一段時間就浮到水面上,冒出頭來吸一口氣。你結果臉色慘白,你在我眼前溺水。」接著,她語氣稍見緩和,「萊諾,注意看,我來教你呼吸。」羅莎跨出一隻腳,重心往前移時吐氣。「懂嗎?」「懂。」我答。「那麼我們就來練習呼吸……把手給我。我們走到茶几的位置。」我們就這麼做樣,手拉著手,我把探路的大腳趾按進地毯裡,邊往前邊吐氣。「當然,我們動作比較誇張,」她說,「不過,呼吸能夠塑造我們的舞步,讓它更有個性。還有最後一件事,麻煩你朝地板吐氣,我是無所謂啦。」
隔天晚上我們跳完一支舞,等著繼續下一支時,羅莎說,「技術不是全部,坦白說,你一個月內就能學會,但要跳出那種感覺……嗯,可能要花上好幾年,是一輩子的功課。」她想必發現她這番話讓我多洩氣,因此馬上又提出另一個更能提振士氣的時間表。她說,「如果一支舞結束之前你還沒墜入情海,那你等於沒跳探戈。」
「一支舞?」我質疑。這話即使出自羅莎口中,仍舊太誇張。「一支舞可能只有三分鐘。」
「或更短。」
「或更長。」
「對,有可能。當然,視情況而定。」
「三分鐘就墜入情海?」
這段日子以來我覺得自己的飯碗穩固多了,所以沒有刻意隱藏我的半信半疑。
「那是事實。」她說。
「哦,是事實,那麼妳能證明?畢竟所謂的事實……」
「萊諾,我知道什麼叫事實。我知道這是真的,因為它確實發生過。」
「在妳身上?」
「不是,」她語帶謹慎,「不是我……」
她噘起嘴唇,正準備開口說些什麼,卻又改變心意,欲言又止。她的注意力轉移到第十四桌,露出不悅神色。「萊諾,那邊是不是有個餐盤沒收走?」
赫克特先生是羅莎指定的老師,我覺得我必須另尋名師,不為別的,只為顯示我的自主性。
哈利.辛格是個自行車騎士兼退休果菜商,他在一家印度餐館樓上的舞蹈教室授課。他有個合作夥伴,是個年紀較輕的外國人,叫費德里科,負責教導舞齡比較久的學生。
- 赫克特先生無論動作或說明都更為精準,哈利比較像果菜行老闆,在貨架和櫃台之間來回奔走。「好,我們試試這個……」他的手在空中抓扒,召喚志願舞伴。他不太擅長記名字,可是如果他盯得夠久,慌張地望著正確的方向,遲早會有位女士從費德里科那群學生裡出來,不甘不願地走到後段班這個角落來。
「好,妳做這個動作,像這樣,跟在我後面。」
我變成第三個舞者,果菜行老闆背後的影子,模仿他的步伐。他瘦削的臉轉過來查看檢查,糾正我,他會說:「像這樣。」於是我透過哈利這種「跟我這樣做」的模式學會了「勾腿」,也就是女士把腳跟甩進你往前伸的腿裡。哈利提出警告:「有些人不喜歡這個。我個人是無所謂,只要她不用我的長褲擦她的鞋底。」這番話引起一陣緊張的咯咯笑。
哈利還教了我搖滾旋轉,是他自己發想的舞步,我發現它跟探戈一點都沾不上邊。他跟黛安一起示範。黛安是個金髮小個子,言談舉止很能給人安定感。「我簡直不敢相信你第一次跳舞。」她說。我當然撒了個小謊。還有一次我引導她在我臂彎裡轉圈,她甚至拍手叫好。「好,非常好。我隨時可以跟你搭檔。」可惜哈利並不滿意。他雙手抱胸,不以為然地板著臉。「最後那個旋轉,」他說,「距離太遠。你的手要平貼在女伴背部,讓她們繞著它轉。」他跟黛安示範一次,哈利的手從她的背、腰,繞到前面。他眨眨眼,「一旦你把女伴擁進懷裡,就別再讓她們逃開。」
我試過帶羅莎做這個舞步,我帶到旋轉時,察覺到她的抗拒。我們轉了半圈就卡住,她不解地瞄了我一眼。「這是什麼?你想做什麼?」一副我提出了很失禮的建議似地,她拿開我的手。
我沒跟她提起哈利的舞蹈課。我不想讓她知道我「背著她」去跟別人學,不希望她覺得我對她的選擇沒信心,或者我認為赫克特先生教得不好。
她狐疑地看著我。
「只是即興發揮,」我說。
「你可以即興發揮,當然,這就是探戈精神,不過能不能等你把舞步都學會以後?」
「好。」
我們重新開始八字我們重新開始8字步和閉式舞姿,然後羅莎說了我一頓。她對男女關係的見解跟哈利南轅北轍,「你不可以圈禁女士,不過你可以施力。」接下來的曲子是〈阿根廷人〉(LosArgentinos),羅莎卻馬上停下來。「看著我的眼睛,你沒在看我。」
「我覺得有。」
「不,你沒有。」
「我覺得……」
「所以你是打算跟鏡子爭辯。」
我閉上嘴。
她說,「如果你視線望向我後面,會失去平衡。」她又跟我解釋,親密感是很實際的事,就跟綁鞋帶一樣,沒什麼好害怕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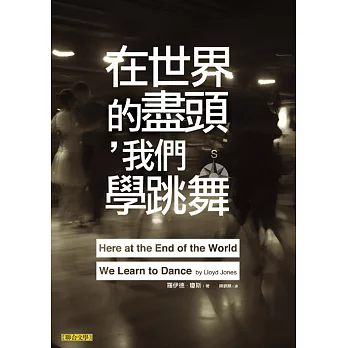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